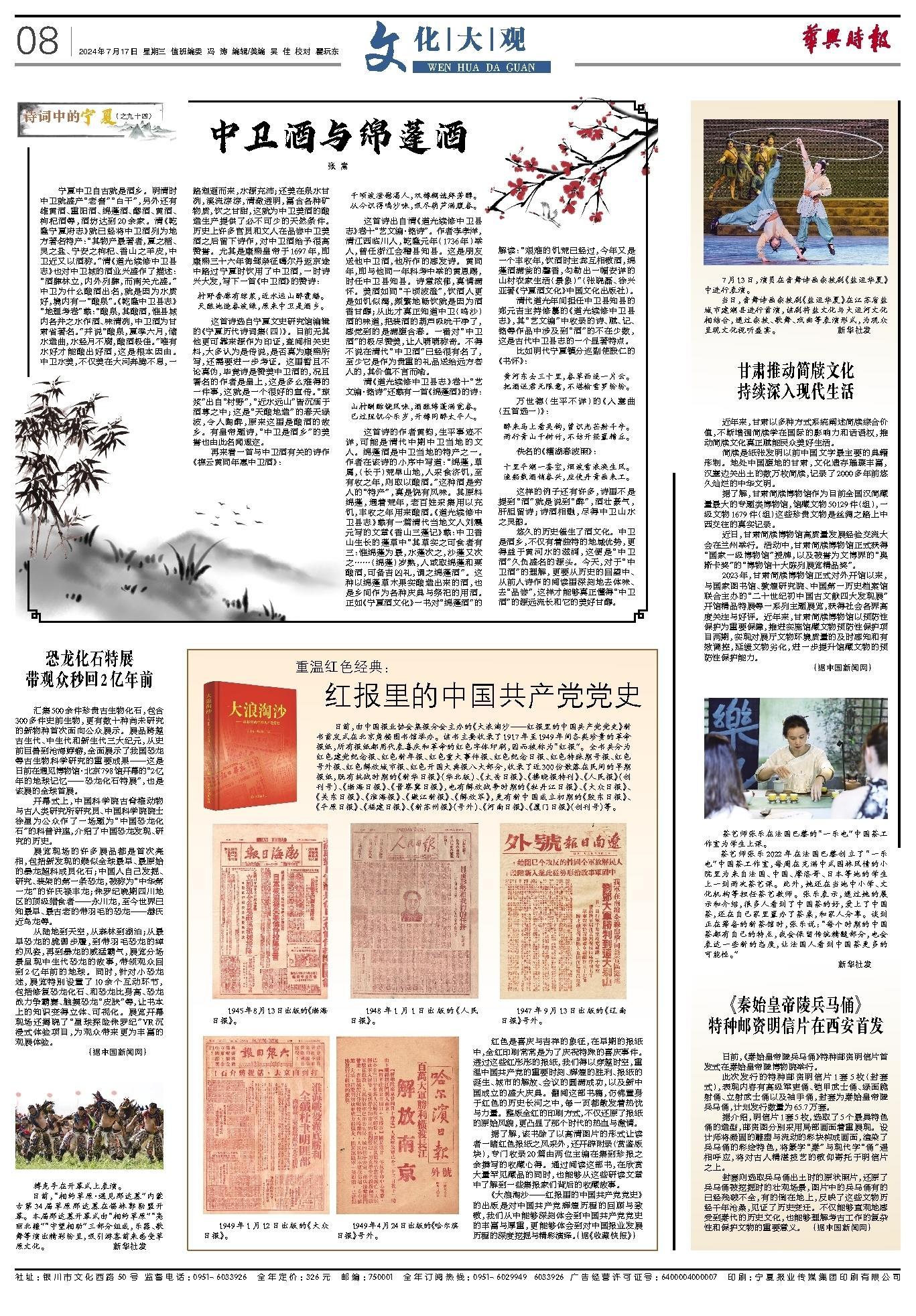张 嵩
宁夏中卫自古就是酒乡。明清时中卫就盛产“老窖”“白干”,另外还有雄黄酒、重阳酒、绵蓬酒、醪酒、黄酒、枸杞酒等,酒坊达到20余家。清《乾隆宁夏府志》就已经将中卫酒列为地方著名特产:“其物产最著者,夏之稻、灵之盐、宁安之枸杞、香山之羊皮,中卫近又以酒称。”清《道光续修中卫县志》也对中卫城的酒业兴盛作了描述:“酒肆林立,内外列肆,而南关尤盛。”中卫为什么酿酒出名,就是因为水质好,境内有一“酿泉”。《乾隆中卫县志》“地理考卷”载:“酿泉,其酿酒,惟县城内各井之水作酒、味清冽,中卫酒为甘肃省著名。”并说“酿泉,夏季六月,储水造曲,水经月不腐,酿酒极佳。”唯有水好才能酿出好酒,这是根本因由。中卫水美,不仅美在大河奔腾不息,一路迤逦而来,水源充沛;还美在泉水甘冽,溪流淙淙,清澈透明,富含各种矿物质,饮之甘甜,这就为中卫美酒的酿造生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天然条件。历史上许多官员和文人在品尝中卫美酒之后留下诗作,对中卫酒给予很高赞誉。尤其是康熙皇帝于1697年,即康熙三十六年御驾亲征噶尔丹返京途中路过宁夏时饮用了中卫酒,一时诗兴大发,写下一首《中卫酒》的赞诗:
村野香廓有琼浆,近水远山醉霞觞。
天酿地造春波绿,原来中卫是酒乡。
这首诗选自宁夏文史研究馆编辑的《宁夏历代诗词集(四)》。目前无其他更可靠来源作为印证,查阅相关史料,大多认为是传说,是否真为康熙所写,还需要进一步考证。这里暂且不论真伪,毕竟诗是赞美中卫酒的,况且署名的作者是皇上,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琼浆”出自“村野”,“近水远山”皆沉湎于酒尊之中;这是“天酿地造”的春天绿波,令人陶醉,原来这里是酿酒的故乡。有皇帝题诗,“中卫是酒乡”的美誉也由此名闻遐迩。
再来看一首与中卫酒有关的诗作《樵云黄同年惠中卫酒》:
千顷波澄慰渴人,双樽稠迭拜芳醇。
从今识得鸣沙味,吸尽葫芦满腹春。
这首诗出自清《道光续修中卫县志》卷十“艺文编·铭诗”。作者李孝洋,清江西临川人,乾隆元年(1736年)举人,曾任浙江会稽县知县。这是朋友送他中卫酒,他所作的感发诗。黄同年,即与他同一年科考中举的黄恩赐,时任中卫县知县。诗意浓郁,真情满怀。美酒如同“千顷波澄”,饮酒人更是如饥似渴,频繁地畅饮就是因为酒香甘醇;从此才真正知道中卫(鸣沙)酒的味道,把装酒的葫芦吸吮干净了,感觉到的是满腹含春。一番对“中卫酒”的极尽赞美,让人啧啧称奇。不得不说在清代“中卫酒”已经很有名了,至少它是作为贵重的礼品送给远方客人的,其价值不言而喻。
清《道光续修中卫县志》卷十“艺文编·铭诗”还载有一首《绵蓬酒》的诗:
山村酬酢饶风味,酒酿绵蓬满瓮春。
已过阻饥今乐岁,开樽同醉太平人。
这首诗的作者黄钧,生平事迹不详,可能是清代中期中卫当地的文人。绵蓬酒是中卫当地的特产之一。作者在该诗的小序中写道:“绵蓬,草属,(长于)荒旱山地,人采食济饥,至有收之年,则取以酿酒。”这种酒是穷人的“特产”,真是饶有风味。其原料绵蓬,遇着荒年,老百姓采集用以充饥,丰收之年用来酿酒。《道光续修中卫县志》载有一篇清代当地文人刘震元写的文章《香山三蓬记》载:中卫香山生长的蓬草中“其草实之可食者有三:惟绵蓬为最,水蓬次之,沙蓬又次之……(绵蓬)岁熟,人或取绵蓬和粟酿酒,可备吉凶礼,谓之绵蓬酒”。这种以绵蓬草木果实酿造出来的酒,也是乡间作为各种庆典与祭祀的用酒。正如《宁夏酒文化》一书对“绵蓬酒”的解读:“艰难的饥荒已经过,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饮酒时主宾互相敬酒,绵蓬酒满瓮的馨香,勾勒出一幅安详的山村农家生活(景象)”(张晓磊、徐兴亚著《宁夏酒文化》中国文化出版社)。
清代道光年间担任中卫县知县的郑元吉主持修纂的《道光续修中卫县志》,其“艺文编”中收录的诗、赋、记、铭等作品中涉及到“酒”的不在少数,这是古代中卫县志的一个显著特点。
比如明代宁夏镇分巡副使殷仁的《书怀》:
黄河东去三十里,春草西连一片云。
把酒送君无限意,不堪榆雪罗纷纷。
万世德(生平不详)的《入塞曲(五首选一)》:
醉来马上看吴钩,曾识光芒射斗牛。
两行青山千树竹,不妨开径置糟丘。
佚名的《糟湖春波照》:
十里平湖一鉴空,烟波雪浪涣生风。
渔船载酒销春兴,应使丹青画未工。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诗里不是提到“酒”就是说到“醉”,酒壮豪气,肝胆留诗;诗酒相融,尽得中卫山水之灵韵。
悠久的历史催生了酒文化。中卫是酒乡,不仅有着独特的地域优势,更得益于黄河水的滋润,这便是“中卫酒”久负盛名的源头。今天,对于“中卫酒”的理解,更要从历史的回望中、从前人诗作的阅读里深刻地去体味、去“品尝”,这样才能够真正懂得“中卫酒”的源远流长和它的美好甘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