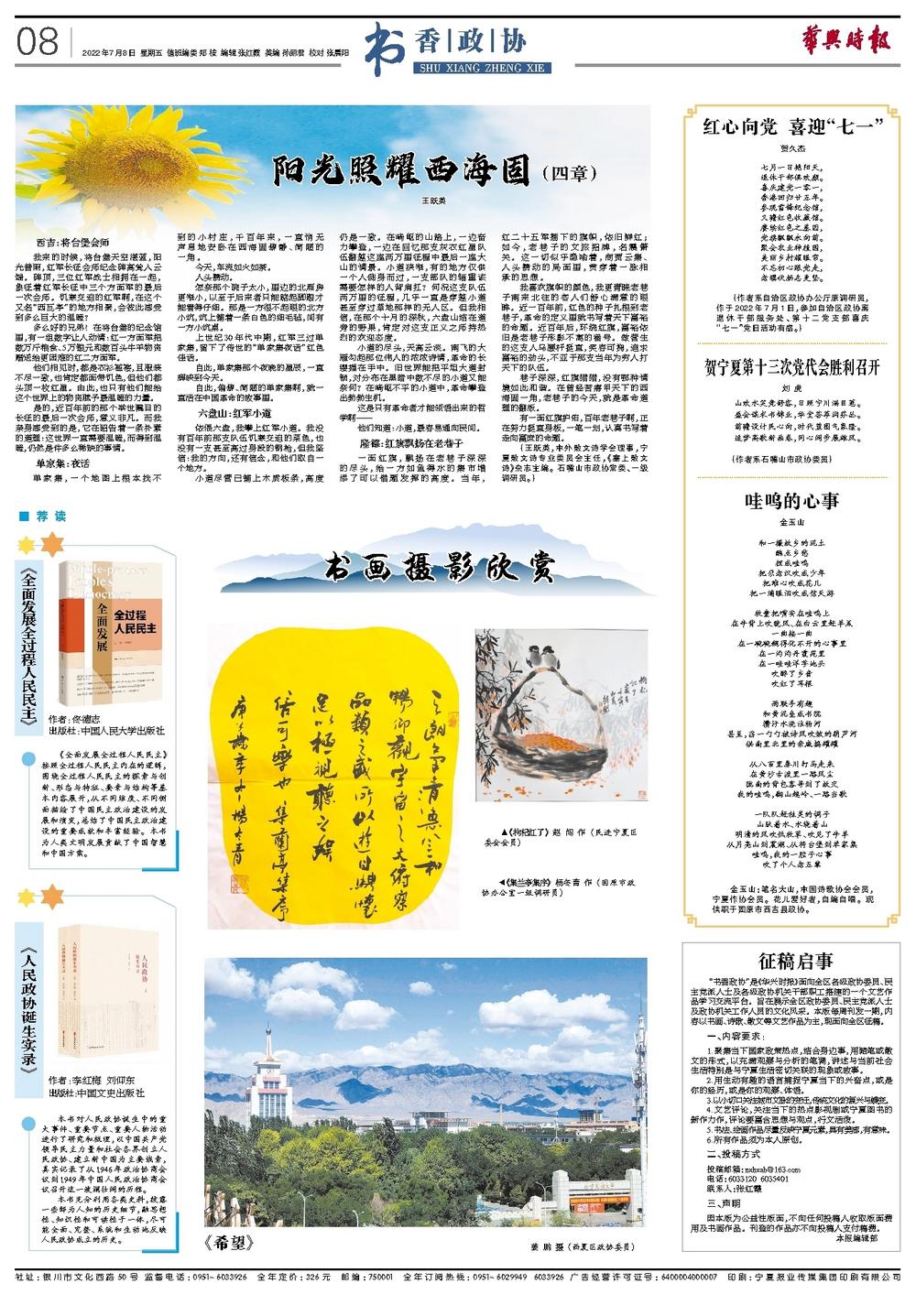我来的时候,将台堡天空湛蓝,阳光普照,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高耸入云端。碑顶,三位红军战士相拥在一起,象征着红军长征中三个方面军的最后一次会师。饥寒交迫的红军啊,在这个又名“西瓦亭”的地方相聚,会彼此感受到多么巨大的温暖?
多么好的兄弟!在将台堡的纪念馆里,有一组数字让人动情:红一方面军把数万斤粮食、5万银元和数百头牛羊物资赠送给更困难的红二方面军。
他们相见时,都是衣衫褴褛,且服装不尽一致,也肯定都面带饥色,但他们都头顶一枚红星。由此,也只有他们能给这个世界上的物资赋予最温暖的力量。
是的,近百年前的那个举世瞩目的长征的最后一次会师,意义非凡。而我亲身感受到的是,它在昭告着一条朴素的道理:这世界一直需要温暖,而得到温暖,仍然是件多么稀缺的事情。
单家集:夜话
单家集,一个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小村庄,千百年来,一直悄无声息地安卧在西海固僻静、简陋的一角。
今天,车流如火如荼。
人头攒动。
怎奈那个院子太小,里边的北厢房更窄小,以至于后来者只能踮起脚跟才能看得仔细。那是一方很不起眼的北方小炕,炕上铺着一条白色的细毛毡,间有一方小炕桌。
上世纪30年代中期,红军三过单家集,留下了传世的“单家集夜话”红色佳话。
自此,单家集那个夜晚的星辰,一直辉映到今天。
自此,偏僻、简陋的单家集啊,就一直活在中国革命的故事里。
六盘山:红军小道
依偎六盘,我攀上红军小道。我没有百年前那支队伍饥寒交迫的菜色,也没有一支甚至高过身段的钢枪,但我坚信:我的方向,还有信念,和他们取自一个地方。
小道尽管已铺上木质板条,高度仍是一致。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边奋力攀登,一边在回忆那支灰衣红星队伍翻越这座两万里征程中最后一座大山的情景。小道狭窄,有的地方仅供一个人侧身而过,一支部队的辎重该需要怎样的人背肩扛?何况这支队伍两万里的征程,几乎一直是穿越小道甚至穿过草地那样的无人区。但我相信,在那个十月的深秋,六盘山结在道旁的野果,肯定对这支正义之师持热烈的欢迎态度。
小道的尽头,天高云淡。南飞的大雁勾起那位伟人的浓浓诗情,革命的长缨握在手中。旧世界能把平坦大道封锁,对分布在黑暗中数不尽的小道又能奈何?在崎岖不平的小道中,革命攀登出勃勃生机。
这是只有革命者才能领悟出来的哲学啊——
他们知道:小道,最容易通向民间。
隆德:红旗飘扬在老巷子
一面红旗,飘扬在老巷子深深的尽头,给一方如鱼得水的集市增添了可以借题发挥的高度。当年,红二十五军插下的旗帜,依旧鲜红;如今,老巷子的文旅招牌,名震箫关。这一切似乎隐喻着,商贾云集、人头攒动的局面里,贯穿着一脉相承的思想。
我喜欢旗帜的颜色,我更青睐老巷子南来北往的客人们舒心满意的眼眸。近一百年前,红色的种子扎根到老巷子,革命的定义里就书写着天下富裕的命题。近百年后,环绕红旗,富裕依旧是老巷子形影不离的番号。做营生的这支人马腰杆挺直,笑容可掬,追求富裕的劲头,不亚于那支当年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巷子深深,红旗猎猎,没有哪种情境如此和谐。在曾经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一角,老巷子的今天,就是革命道理的翻版。
有一面红旗护佑,百年老巷子啊,正在努力挺直身板,一笔一划,认真书写着走向富庶的命题。
(王跃英,中外散文诗学会理事,宁夏散文诗专业委员会主任,《塞上散文诗》杂志主编。石嘴山市政协常委、一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