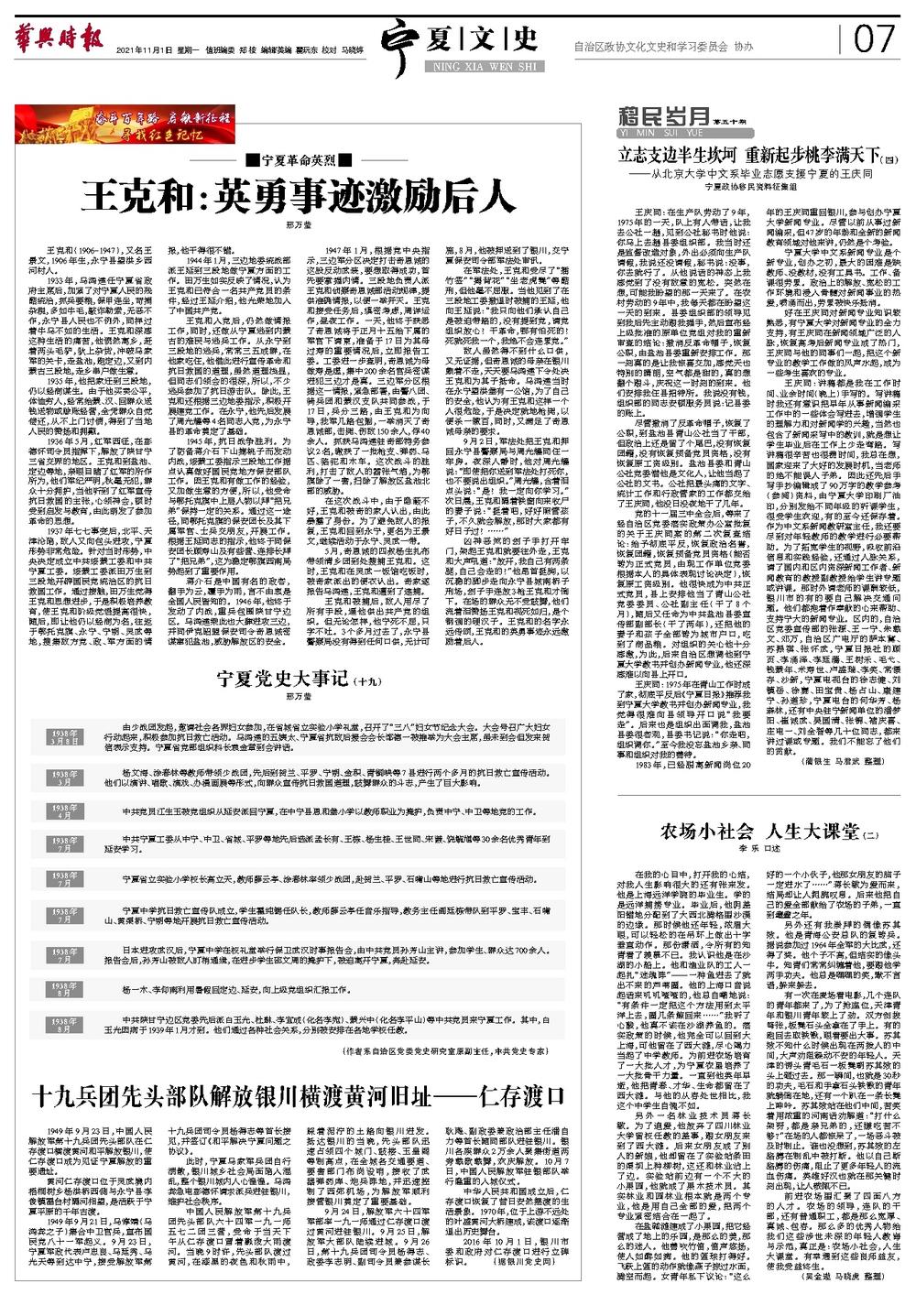李 乐 口述
在我的心目中,打开我的心结,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的还有张来发。他是上海远洋学院的毕业生。学的是远洋捕捞专业。毕业后,他阴差阳错地分配到了大西北腾格里沙漠的边缘。那时候他还年轻,浓眉大眼,可以轻松的在吊环上做出十字垂直动作。那份潇洒,令所有的知青看了羡慕不已。我认识他是在沙湖的小船上。他和渔业队的工人一起扎“迷魂阵”——一种鱼进去了就出不来的芦苇圈。他的上海口音说起话来叽叽喳喳的,他总自嘲地说:“有条件一定把这个方法用到太平洋上去,圈几条鲸回来……”我听了心酸,他真不该在沙湖养鱼的。落实政策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回到大上海,可他留在了西大滩,尽心竭力当起了中学教师。为前进农场培育了一大批人才,为宁夏农垦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一直到他英年早逝,他把青春、才华、生命都留在了西大滩。与他的从容处世相比,我这个中学生自愧不如。
另外一名林业技术员蒋长敏。为了追爱,他放弃了四川林业大学留校任教的差事,跟女朋友来到了西大滩。后来女朋友成了别人的新娘,他却留在了实验站条田的渠坝上种柳树,这还和林业沾上了边。实验站前边有一个不大的小果园,他就成了果木技术员。其实林业和园林业根本就是两个专业,他是用自己全部的爱,把两个专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在盐碱滩建成了小果园,把它经营成了地上的乐园,是那么的美,那么的迷人。他善吹竹笛,笛声悠扬,使人如醉如痴。他的篮球打得好。飞跃上篮的动作就像燕子掠过水面,腾空而起。女青年私下议论:“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他那女朋友的脑子一定进水了……”蒋长敏为爱而来,结局却让人扼腕叹息。后来他把自己的爱全部献给了农场的子弟,一直到耄耋之年。
另外还有我崇拜的偶像苏其效。他是青海公安总队的复转兵。据说参加过1964年全军的大比武,还得了奖。他个子不高,但结实的像头牛。知青们常常纠缠着他,要跟他学两手功夫。他总是嘿嘿的笑,默不言语,躲来躲去。
有一次在麦场看电影,几个连队的青年都来了,为了抢座位,天津青年和银川青年较上了劲。双方剑拔弩张,板凳石头全拿在了手上。有的跑回去取铁锹,眼看要出大事。苏其效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两拨人的中间,大声劝阻躁动不安的年轻人。天津的愣头青毛石一板凳朝苏其效的头上砸过去。那一瞬间,也就是30秒的功夫,毛石和手拿石头铁锹的青年就躺倒在地,还有一个趴在一条长凳上呻吟。苏其效站在他们中间,苦笑着用浓重的河南话劝解道:“打什么架呀,都是亲兄弟的,还嫌吃苦不够?”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一场恶斗被及时制止。谁也没想到,苏其效的左胳膊在制乱中被打断。他以自己断胳膊的伤痛,阻止了更多年轻人的流血伤痛。英雄好汉也就在那关键时刻出现,让人敬佩不已。
前进农场里汇聚了四面八方的人才。农场的领导,连队的干部,还有普通职工,都是那么宽厚、真诚、包容。那么多的优秀人物给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教诲与示范,真正是:农场小社会,人生大课堂。有幸遇到这些良师益友,使我受益终生。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