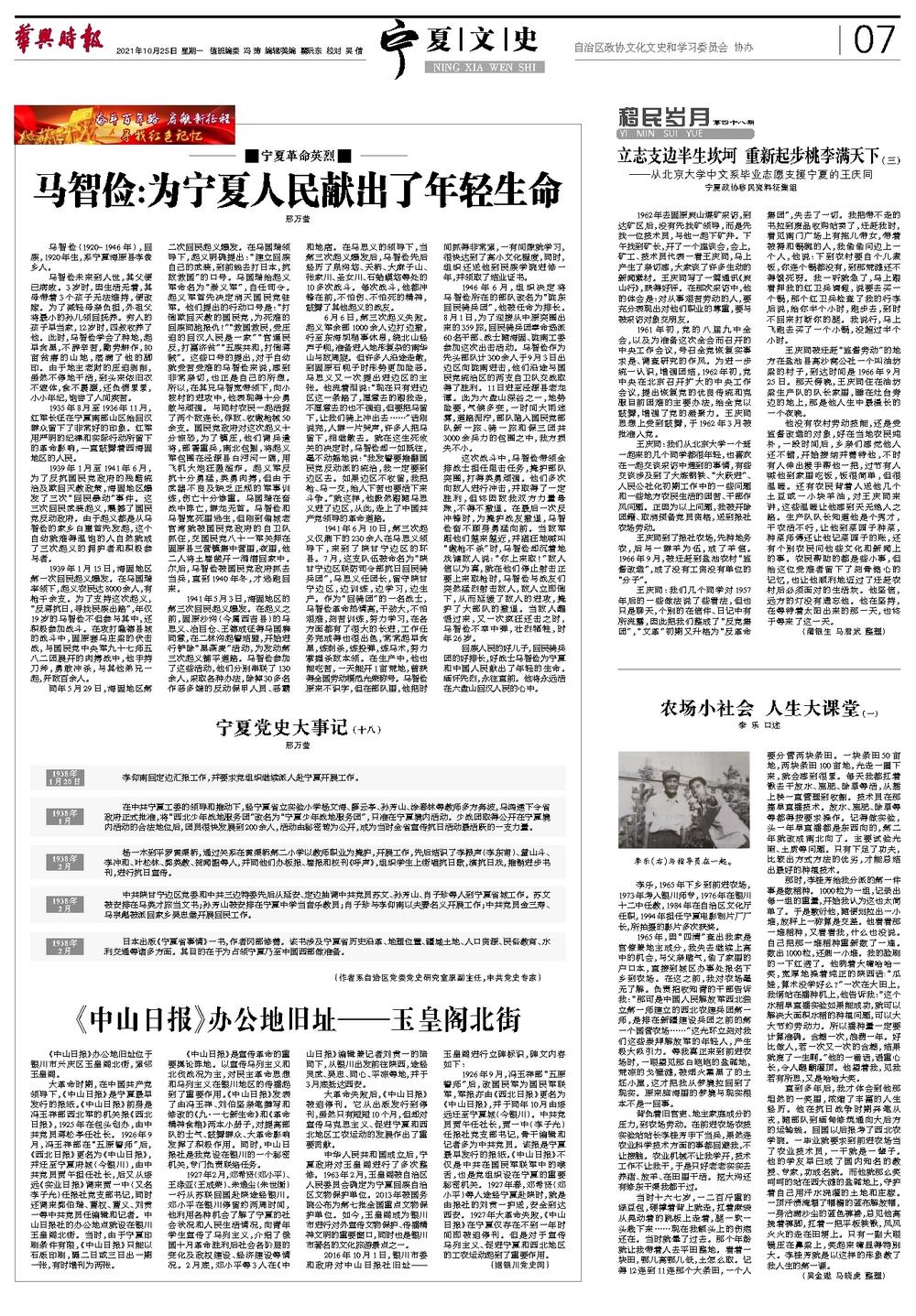李 乐 口述
李乐,1965年下乡到前进农场,1973年考入银川师专,1976年在银川十二中任教,1984年在自治区文化厅任职,1994年担任宁夏电影制片厂厂长,所拍摄的影片多次获奖。
1965年,因“四清”查出我家是官僚兼地主成分,我失去继续上高中的机会,与父亲赌气,偷了家里的户口本,直接到城区办事处报名下乡到农场。在这之前,我对农场毫无了解。负责招收知青的干部告诉我:“那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一师建立的西北农建兵团第一师,是排在新疆建设兵团之前的第一个国营农场……”这光环立刻对我们这些崇拜解放军的年轻人,产生极大吸引力。等我真正来到前进农场时,一眼望见那白皑皑的盐碱地,荒凉的戈壁滩,被烟火熏黑了的土坯小屋,这才把我从梦境拉回到了现实。原来脑海里的梦境与现实根本不是一回事。
背负着旧官吏、地主家庭成分的压力,到农场劳动。在前进农场农技实验站站长李桂芳手下当兵,果然连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事都回避我,不让接触。农业机械不让我学开,技术工作不让我干,于是只好老老实实去养猪、放羊、在田里干活。挖大沟还有修东干渠我都干过。
当时十六七岁,一二百斤重的绿豆包,硬撑着背上就走,扛着麻袋从晃动着的跳板上走着,腿一软一头栽下来……现在我额头上的伤疤还在。当时就晕了过去。那个年龄就让我带着人去平田整地。看着一块田,哪儿高哪儿低,土怎么取。记得12连到11连那个大条田,一个人要分管两块条田。一块条田50亩地,两块条田100亩地,光走一圈下来,就会感到很累。每天我都扛着锹去干放水、施肥、除草等活,从插上秧一直管理到收割。技术员在那搞旱直播技术。放水、施肥、除草等等都得按要求操作。记得做实验,头一年旱直播都是东西向的,第二年就改成南北向了。主要试验光照、土质等问题。只有下足了功夫,比较出方式方法的优劣,才能总结出最好的种植技术。
那时,李桂芳给我分派的第一件事是数稻种。1000粒为一组,记录出每一组的重量,开始我认为这也太简单了。于是敷衍他,随便划拉出一小堆,放秤上一称算是交差。他看看那一堆稻种,又看看我,什么也没说。自己把那一堆稻种重新数了一遍。数出1000粒,还剩一小堆。我的脸刷的一下红透了。他咧着大嘴哈哈一笑,宽厚地操着纯正的陕西话:“瓜娃,算术没学好么?”一次在大田上,我俩站在播种机上,他告诉我:“这个水稻旱直播实验如果能成功,就可以解决大面积水稻的种植问题,可以大大节约劳动力。所以播种量一定要计算准确。含糊一次,浪费一年。好比做人,若一次又一次的含糊,结果就废了一生啊。”他的一番话,语重心长,令人醍醐灌顶。他望着我,见我若有所思,又是哈哈大笑。
直到多年后,我才体会到他那坦然的一笑里,浓缩了丰富的人生经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弃笔从戎,随部队到缅甸修筑通向大后方的运输线。回国以后报考了西北农学院。一毕业就要求到前进农场当了农业技术员,一干就是一辈子。他的学友早已成了国内知名的教授、专家,功成名就。而他就那么笑呵呵的站在西大滩的盐碱地上,守护着自己用汗水浇灌的土地和庄稼。一顶汗渍淹塌了帽檐的蓝布解放帽,一身沾满沙尘的蓝色裤褂,总见他高挽着裤脚,扛着一把平板铁锹,风风火火的走在田埂上。只有一副大眼镜压在鼻梁上,笑起来嘴显得特别大。李桂芳就是以这样的形象教了我人生的第一课。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