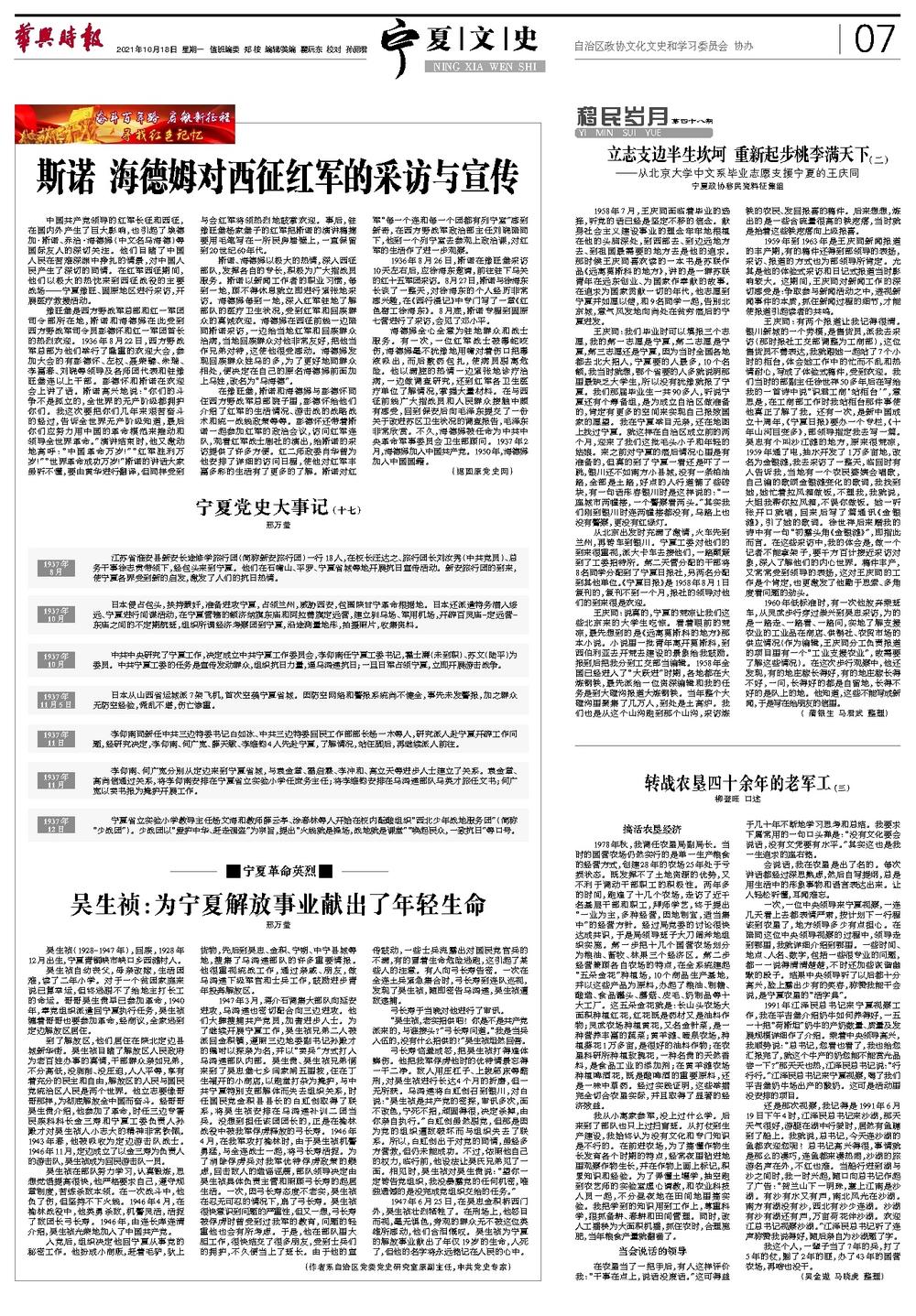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1958年7月,王庆同面临着毕业的选择,听党的话已经是坚定不移的信念。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理念牢牢地根植在他的头脑深处,到西部去、到边远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他的追求。那时候王庆同喜欢读的一本书是苏联作品《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讲的是一群苏联青年在远东创业、为国家作奉献的故事。在追求为国家贡献一切的年代,他志愿到宁夏并如愿以偿,和9名同学一起,告别北京城,意气风发地向尚处在贫穷落后的宁夏进发。
王庆同:我们毕业时可以填报三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宁夏,第二志愿是宁夏,第三志愿还是宁夏,因为当时全国各地都去北大招人,宁夏要的人最多,10个名额,我当时就想,哪个省要的人多就说明那里最缺乏大学生,所以没有犹豫就报了宁夏。我们那届毕业生一共90多人,听说宁夏还有个筹备组,是为成立自治区做准备的,肯定有更多的空间来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的愿望。我在宁夏举目无亲,还在地图上找过宁夏。就这样在自治区成立前的两个月,迎来了我们这批毛头小子和年轻的姑娘。来之前对宁夏的落后情况心里是有准备的,但真的到了宁夏一看还是吓了一跳,银川还不如南方小县城,没有一条柏油路,全部是土路,好点的人行道铺了些砖块,有一句话形容银川时是这样说的:“一座城市两幢楼,一个警察看两头。”其实我们刚到银川时连两幢楼都没有,马路上也没有警察,更没有红绿灯。
从北京出发时充满了激情,火车先到兰州,再转车到银川。宁夏工委对他们的到来很重视,派大卡车去接他们,一路颠簸到了工委招待所。第二天管分配的干部将8名同学分配到了宁夏日报社,另两名分配到其他单位。《宁夏日报》是1958年8月1日复刊的,复刊不到一个月,报社的领导对他们的到来很是欢迎。
王庆同:说真的,宁夏的荒凉让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大学生吃惊。看着眼前的荒凉,最先想到的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那本小说。小说里一批青年离开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去开荒去建设的景象给我鼓励。报到后把我分到工交部当编辑。1958年全国已经进入了“大跃进”时期,各地都在大炼钢铁,最先派给一位资深编辑和我的任务是到大磴沟报道大炼钢铁。当年整个大磴沟里聚集了几万人,到处是土高炉。我们也是从这个山沟跑到那个山沟,采访炼铁的农民、发回报喜的稿件。后来想想,炼出的是一些含硫量很高的铁疙瘩,当时就是抬着这些铁疙瘩向上级报喜。
1959年到1963年是王庆同新闻报道的丰产期,有的稿件还得到部领导的表扬,采访、报道的方式也为部领导所肯定。尤其是他的体验式采访和日记式报道当时影响较大。这期间,王庆同对新闻工作的深切感受是:争取参与新闻活动之中,透视新闻事件的本质,抓住新闻过程的细节,才能使报道引起读者的共鸣。
王庆同:有两个报道让我记得很清。银川新城的一个劳模,是售货员,派我去采访(那时报社工交部调整为工商部),这位售货员不善表达,我就跟她一起站了7个小时的柜台,体会她工作中的忙而不乱和热情耐心,写成了体验式稿件,受到欢迎。我们当时的部副主任徐世祥50多年后在写给我的一首诗中说“识君工商‘站柜台’”,意思是,在工商部工作时我站柜台那件事使他真正了解了我。还有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宁夏日报》要办一个专栏,《十年山河巨变多》,部领导指定我去写一篇。吴忠有个叫沙江滩的地方,原来很荒凉,1959年通了电,抽水开发了1万多亩地,改名为金银滩,我去采访了一整天,临回时有人告诉我,当地有一个农民婆姨会唱歌,自己编的歌颂金银滩变化的歌词,我找到她,她忙着拉风箱做饭,不理我,我就说,大姐我帮你拉风箱,不误你做饭。她一听张开口就唱,回来后写了篇通讯《金银滩》,引了她的歌词。徐世祥后来赠我的诗中有一句“初露头角《金银滩》”,即指此而言。在这些采访中,我的体会是,做一个记者不能拿架子,要千方百计接近采访对象,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稿件丰产,又常常受到领导的表扬,这对王庆同的工作是个肯定,也更激发了他勤于思索、多角度看问题的劲头。
1960年低标准时,有一次他放弃乘班车,从灵武步行穿过崇兴到吴忠采访,为的是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实地了解支援农业的工业品在商店、供销社、农贸市场的供应情况(作为编辑,王庆同分工负责报道的项目里有一个“工业支援农业”,故需要了解这些情况)。在这次步行观察中,他还发现,有的地庄稼长得好,有的地庄稼长得不好,一问,长得好的都是自留地,长得不好的是队上的地。他知道,这些不能写成新闻,于是写在给朋友的信里。
(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