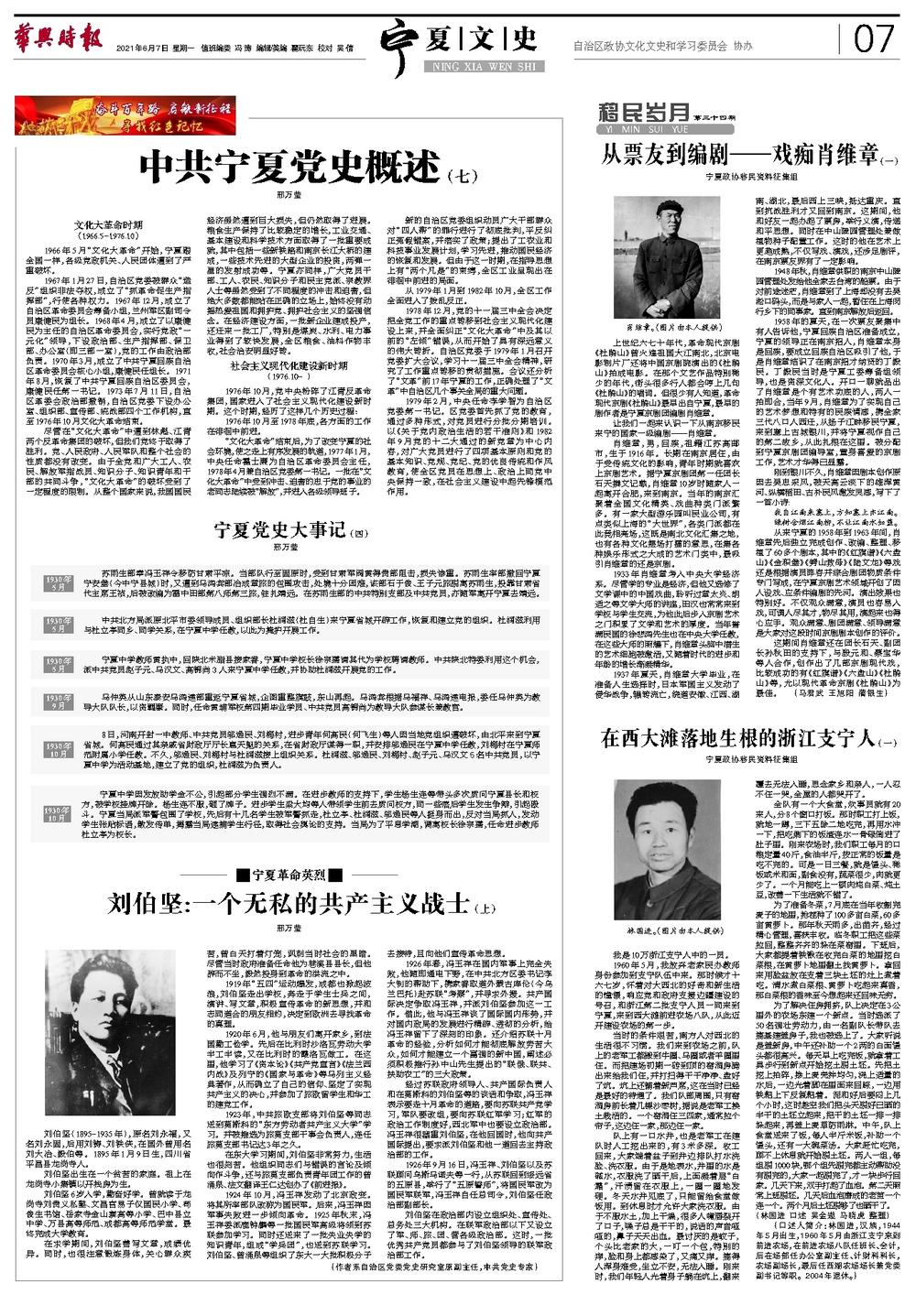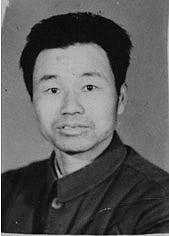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我是10万浙江支宁人中的一员。
1960年5月,我放弃老家民办教师身份参加到支宁队伍中来。那时候才十六七岁,怀着对大西北的好奇和新生活的憧憬,响应党和政府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和浙江第二批支宁人员一同来到宁夏,来到西大滩前进农场八队,从此迈开建设农场的第一步。
当时的条件艰苦,南方人对西北的生活很不习惯。我们来到农场之前,队上的老军工都搬到牛圈、马圈或者羊圈里住。而把建场初期一砖到顶的窑洞房腾出来给我们住,并打扫得干干净净、盘好了炕。炕上还铺着新芦席,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我们队部周围,只有窑洞房前长着几棵沙枣树,据说是老军工换土栽活的。一个窑洞住三四家,通常拉个帘子,这边住一家,那边住一家。
队上有一口水井,也是老军工在建队时人工挖出来的,有3米多深。收工回来,大家端着盆子到井边排队打水洗脸、洗衣服。由于是地表水,井里的水是碱水,衣服洗了晒干后,上面凝着层“白霜”,汗渍留在衣服上,一圈一圈地发硬。冬天水井见底了,只能留给食堂做饭用。到休息时才允许大家洗衣服。由于不服水土,加上干燥,很多人嘴唇裂开了口子,嗓子总是干干的,说话的声音哑哑的,鼻子天天出血。最讨厌的是蚊子,个头比老家的大,一叮一个包,特别的痒,脸和身上都感染了,又痛又痒。搞得人浑身难受,坐立不安,无法入睡。刚来时,我们年轻人光着身子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思念家乡和亲人,一人忍不住一哭,全屋的人都哭开了。
全队有一个大食堂,炊事员就有20来人,分8个窗口打饭。那时职工打上饭,就地一蹲,三下五除二地吃完,再用水冲一下,把吃剩下的饭渣连水一骨碌倒进了肚子里。刚来农场时,我们职工每月的口粮定量40斤,食油半斤,按正常的饭量是吃不完的。可是一日三餐,就是馒头、稀饭或米和面,副食没有,蔬菜很少,肉就更少了。一个月能吃上一顿肉炖白菜、炖土豆,改善一下生活就不错了。
为了准备冬菜,7月底在当年收割完麦子的地里,抢茬种了100多亩白菜,60多亩黄萝卜。那年秋天雨多,出苗齐,经过精心管理,喜获丰收。临冬职工把这些菜拉回,整整齐齐的垛在菜窑里。下班后,大家都提着铁锹在收完白菜的地里挖白菜根,在黄萝卜地里翻土找黄萝卜。拿回来用脸盆放在支着三块土坯的灶上煮着吃。清水煮白菜根、黄萝卜吃起来真香,那白菜根的香味至今想起来还回味无穷。
为了解决住房拥挤,队上决定在3公里外的农场东建一个新点。当时选派了50名强壮劳动力,由一名副队长带队去搞基建盖房子,我也被选上了。大家听说是盖新房,中午还补助一个2两的白面馒头都很高兴。每天早上吃完饭,就拿着工具步行到新点开始挖土脱土坯。先把土挖上拍碎,掺上麦壳拌均匀,浇上适量的水后,一边光着脚在里面来回踩,一边用铁耙上下反复耙着。泥和好后要闷上几个小时,这时趁空我们把头天脱好已晒的半干的土坯立起来,把干的土坯一排一排垛起来,再盖上麦草防雨淋。中午,队上食堂送来了饭,每人半斤米饭,补助一个馒头,还有一大碗菜汤。大家赶忙吃完,顾不上休息就开始脱土坯。两人一组,每组脱1000块,哪个组先脱完都主动帮助没有脱完的,大家一起脱完了,才一块步行回家。几天下来,双手打起了血泡。第二天照常上班脱坯。几天后血泡磨成的老茧一个连一个。两个月后土坯脱够了也晒干了。
(林国进 口述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
(口述人简介:林国进,汉族,1944年5月出生,1960年5月由浙江支宁来到前进农场,在前进农场八队任班长、会计,后在场部任办公室副主任、计财科科长,农场副场长,最后任西湖农场场长兼党委副书记等职。2004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