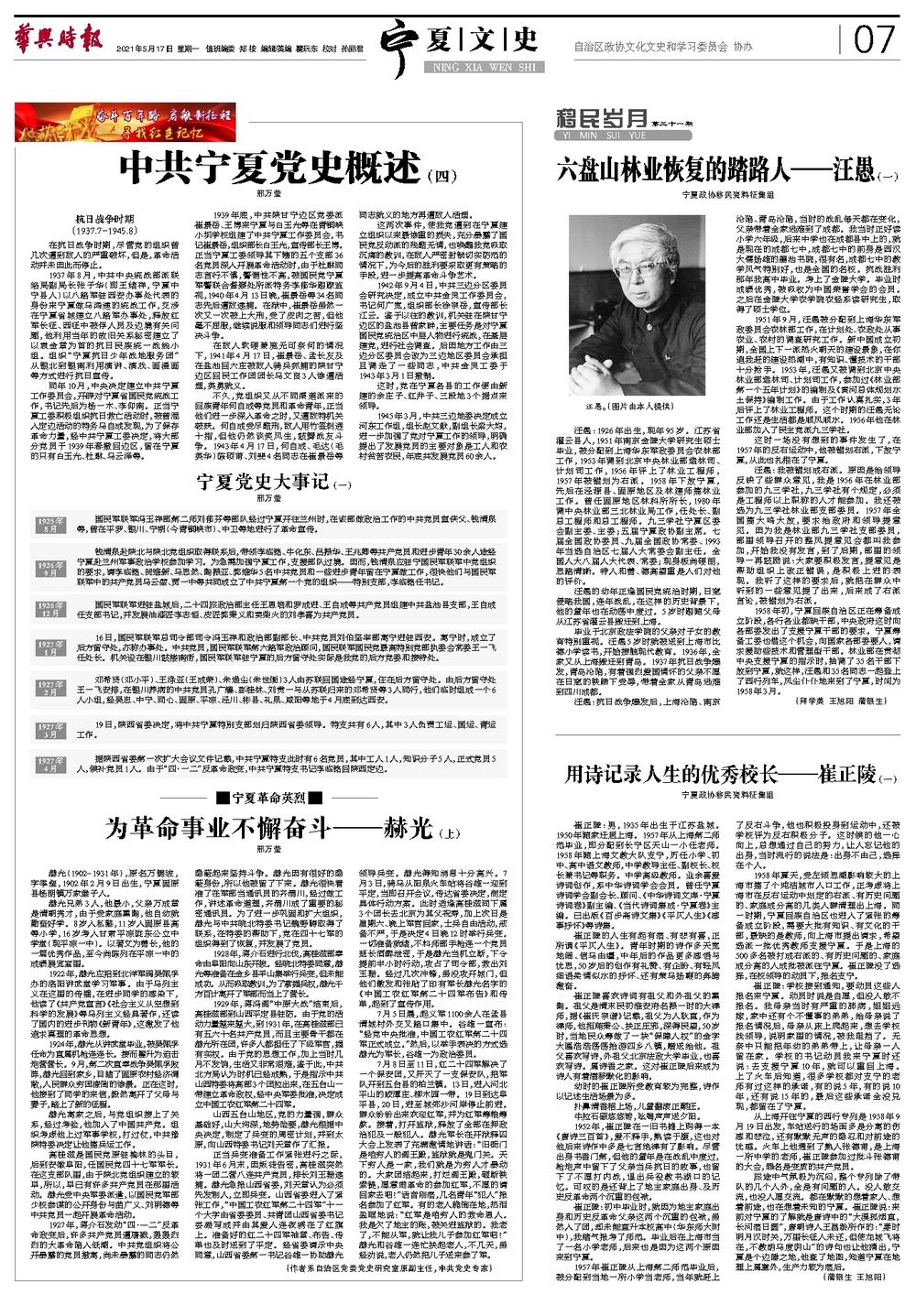邢万莹
赫光(1902-1931年),原名万锡绂,字季玺,1902年2月9日出生,宁夏固原县杨朗镇万家堡子人。
赫光兄弟3人,他最小,父亲万成章是清朝秀才,由于受家庭熏陶,他自幼就勤奋好学。8岁入私塾,11岁入固原县高等小学,16岁考入甘肃平凉陇东公立中学堂(现平凉一中)。以著文为善长,他的一篇优秀作品,至今尚陈列在平凉一中的成绩展览室里。
1922年,赫光应招到北洋军阀吴佩孚办的洛阳讲武堂学习军事。由于马列主义在这里的传播,在进步同学的感染下,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读了国内的进步刊物《新青年》,这激发了他追求真理的革命思想。
1924年,赫光从讲武堂毕业,被吴佩孚任命为直属机枪连连长。接而擢升为迫击炮营营长。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败阵,赫光回到家乡,目睹了固原农村经济凋敝,人民群众穷困潦倒的惨景。正在这时,他接到了同学的来信,毅然离开了父母与妻子,踏上了新的征程。
赫光离家之后,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经过考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考虑他上过军事学校,打过仗,中共豫陕特委决定让他搞兵运工作。
高桂滋是国民党原驻榆林的头目,后到安徽阜阳,任国民党四十七军军长。在这支部队里,由于陕北党组织建立的较早,所以,早已有许多共产党员在那里活动。赫光受中央军委派遣,以国民党军部少校参谋的公开身份与苗广义、刘明德等中共党员一起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二”反革命政变后,许多共产党员遭屠戮,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低潮。中共党组织将公开暴露的党员撤离,尚未暴露的同志仍然隐蔽起来坚持斗争。赫光因有很好的隐蔽身份,所以他被留了下来。赫光很快看准了在军部当通讯员的齐渭川,经过做工作,讲述革命道理,齐渭川成了重要的秘密通讯员。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组织,赫光与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取得了联系,在特委的帮助下,党在四十七军的组织得到了恢复,并发展了党员。
1928年,蒋介石进行北伐,高桂滋部奉命由阜阳向山东开拔。经皖北特委同意,赫光等准备在金乡县羊山集举行兵变,但未能成功。从而吸取教训,为了掌握兵权,赫光千方百计离开了军部而当上了营长。
1929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高桂滋部到山西平定县驻防。由于党的活动力量越来越大,到1931年,在高桂滋部已有五六十名共产党员,而且主要骨干都在赫光所在团,许多人都担任了下级军官,握有实权。由于党的思想工作,加上当时几月不发饷,生活又非常艰难,鉴于此,中共北方局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指示中共山西特委将高部3个团拉出来,在五台山一带建立革命政权,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
山西五台山地区,党的力量强,群众基础好,山大沟深,地势险要,赫光根据中央决定,制定了兵变的周密计划,并到太原,向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作了汇报。
正当兵变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1931年6月末,因叛徒告密,高桂滋突然将一团二营八连共产党员,排长刘玉珊逮捕。赫光急报山西省委,刘天章认为必须先发制人,立即兵变。山西省委进入了紧张工作,“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十一个大字由省委委员、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娄凝写成并由其爱人连夜绣在了红旗上。准备好的红二十四军袖章、布告、传单也及时送到了平定。经省委请示中央同意,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谷雄一协助赫光领导兵变。赫光得知消息十分高兴。7月3日,骑马从阳泉火车站将谷雄一迎到平定,当即召开会议,传达省委决定,商定具体行动方案。此时适逢高桂滋同下属3个团长去北京为其父祝寿,加上次日是星期六、晚上军官回家,士兵自由活动,戒备不严,于是决定4日晚12时举行兵变。一切准备就绪,不料师部手枪连一个党员班长酒醉泄密,于是赫光当机立断,下令提前半小时行动,攻占了司令部,救出刘玉珊。经过几次冲锋,虽没攻开城门,但他们散发和张贴了印有军长赫光名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布告》和传单,起到了宣传作用。
7月5日晨,起义军1100余人在孟县清城村外交叉路口集中。谷雄一宣布:“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正式成立。”然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赫光为军长,谷雄一为政治委员。
7月8日至11日,红二十四军解决了一个保安团,又歼灭了一支保安队,把军队开到五台县的柏兰镇。13日,进入河北平山的蛟潭庄、柳木园一带。19日到达阜平县,20日,进至城郊沙河岸停止前进。群众纷纷出来欢迎红军,并为红军筹粮筹款。接着,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在押政治犯及一般犯人。赫光军长在开狱释囚大会上发表了充满激情地讲话:“旧衙门是咱穷人的阎王殿,监狱就是鬼门关。天下穷人是一家,我们就是为穷人才暴动的。大家团结起来,打烂阎王殿,砸断铁索链,愿意闹革命的参加红军,不愿的请回家去吧!”话音刚落,几名青年“犯人”报名参加了红军。有的老人跪倒在地,热泪盈眶地说:“红军是咱穷人的救命恩人。我是欠了地主的账,被关进监狱的。我老了,不能从军,就让我儿子参加红军吧!”赫光和谷雄一连忙扶起老人,不几天,虽经劝说,老人仍然把儿子送来参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