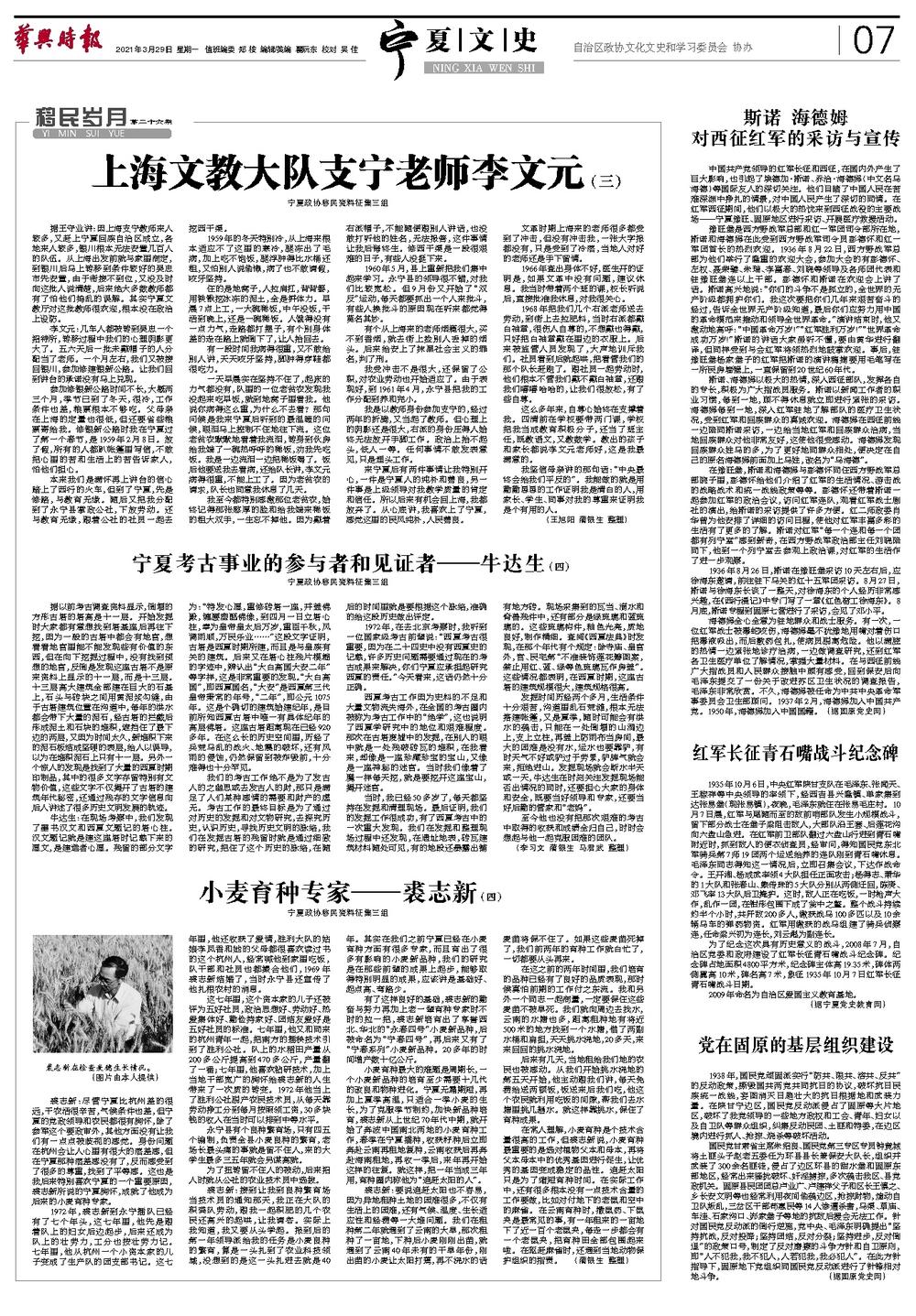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据以前考古调查资料显示,倒塌的方形古塔的塔高是十一层。开始发掘时大家都有意想找到塔基座后再往下挖,因为一般的古塔中都会有地宫,想看看地宫里能不能发现些有价值的东西,但在向下挖掘过程中,没有找到预想的地宫,反倒是发现这座古塔不是原来资料上显示的十一层,而是十三层。十三层高大建筑全部建在巨大的石基上,石头与砖块之间用黄泥浆勾缝,由于古塔建筑位置在沟道中,每年的洪水都会带下大量的泥石,经古塔的拦截后形成泥土和石块的堆积,遮挡住了最下边的两层,又因为时间太久,新堆积下来的泥石板结成坚硬的表层,给人以误导,以为在堆积泥石上只有十一层。另外一个惊人的发现是找到了大量的西夏时期印制品,其中的很多文字存留特别有文物价值,这些文字不仅揭开了古塔的建筑年代秘密,还通过残存的文字信息向后人讲述了很多历史文明发展的轨迹。
牛达生:在现场考察中,我们发现了墨书汉文和西夏文题记的塔心柱。汉文题记就是建这座塔时记载下来的愿文,是建造者心愿。残留的部分文字为:“特发心愿,重修砖塔一座,并盖佛殿,缠腰塑匦佛像,到四月一日立塔心柱,奉为皇帝皇太后万岁,重臣千秋,风调雨顺,万民乐业……”这段文字证明,古塔是西夏时期所建,而且是与皇族有关的建筑。后来又在塔心柱残片模糊的字迹中,辨认出“大白高国大安二年”等字样,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大白高国”,即西夏国名,“大安”是西夏第三代皇帝秉常的年号,“二年”,即公元1075年。这是个确切的建筑始建纪年,是目前所知西夏古塔中唯一有具体纪年的高层佛塔。这座古塔距离现在已经920多年。在这么长的历史空间里,历经了兵荒马乱的战火、地震的破坏,还有风雨的侵蚀,仍然保留到被炸毁前,十分难得也十分罕见。
我们的考古工作绝不是为了发古人的之幽思或去发古人的财,那只是满足了人们某种感情的需要和财产的虚无。考古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为了通过对历史的发掘和对文物研究,去探究历史,认识历史,寻找历史文明的脉络,我们在发掘古塔的残留时就是通过细致的研究,把住了这个历史的脉络,在随后的时间里就是要根据这个脉络,准确的给这段历史做出评定。
1972年,在去北京考察时,我听到一位国家级考古前辈说:“西夏考古很重要,因为在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史的记载,许多历史问题需要通过现在的考古成果来解决,你们宁夏应承担起研究西夏的责任。”今天看来,这话仍然十分正确。
西夏考古工作因为史料的不足和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在全国的考古圈内被称为考古工作中的“绝学”,这也说明了西夏学研究中的地位和艰难程度。那次在古塔废墟中的发掘,在别人的眼中就是一处残破砖瓦的堆积,在我看来,却像是一座珍藏珍宝的宝山,又像是一座神秘的迷宫。当时我们像着了魔一样每天挖,就是要挖开这座宝山,揭开迷宫。
当时,我已经50多岁了,每天都坚持在发掘和清理现场。最后证明,我们的发掘工作很成功,有了西夏考古中的一次重大发现。我们在发掘和整理现场过程中还发现,在遗址地表,砖瓦建筑材料随处可见,有的地段还暴露出铺有地方砖。现场采集到的瓦当、滴水和脊兽残件中,还有部分是绿琉璃和蓝琉璃的。这些琉璃构件,釉色光亮,质地良好,制作精细。查阅《西夏法典》时发现,在那个年代有个规定:除寺庙、皇宫外,官、民宅第“不准装饰莲花瓣图案,禁止用红、蓝、绿等色琉璃瓦作房盖”。这些情况都表明,在西夏时期,这座古塔的建筑规模很大,建筑规格很高。
发掘时间历经两个多月,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沟道里乱石荒滩,根本无法搭建帐篷,又是夏季,随时可能会有洪水的袭击,只能在一处倒塌的山洞边上,支上立柱,再盖上防雨布当房间,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水,运水也要靠驴,有时天气不好或驴过于劳累,驴脾气就会来,拒绝进山。发掘现场就会断水半天或一天,牛达生在时刻关注发掘现场能否出情况的同时,还要担心大家的身体和安全,既要当好领导和专家,还要当好后勤的管家和“老妈”。
至今他也没有把那次艰难的考古中取得的收获和成绩全归自己,时时会想起与他一起克服困难的团队。
(李习文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